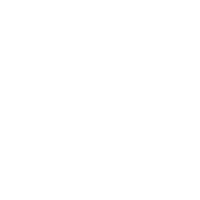我爸特地花8万买奔驰抵押车,直奔西藏无人区,清收队跟到半路返航:不敢收
发布日期:2025-12-31 03:18 点击次数:170
声明:本文根据资料改编创作,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图片非真实画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你疯了?八万块买个过不了户的抵押车?这车随时会被人抢回去!”我把手里的茶杯重重顿在桌上,茶水溅了一手。
老林没看我,只顾着用抹布擦那辆黑色的大奔车标,动作慢得像是在擦家里的那块旧牌位。
“能开就行。”他嗓音沙哑,透着股倔劲。
“你要去哪?这车里还有定位器,那些收车的明天就能找上门!”
老林直起腰,把抹布往引擎盖上一扔,指了指西边的方向:“去那边。有些话,得去那儿说。”

01.
“签字吧。”卖车的胖子把合同推过来,手指缝里夹着根中华,烟灰有一截没一截地掉在桌面上。
老林从怀里掏出老花镜,戴上,手有点抖。他没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免责条款,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按手印。
红印泥沾在他粗糙的拇指上,像块难看的疤。
“爸,这钱是你养老的。”我站在他身后,感觉太阳穴突突地跳。
老林头也不回:“我还没老到动不了。”
胖子数着验钞机里吐出来的红票子,嘴角咧到了耳根:“老爷子爽快。这车况你也看了,当年落地一百多万,现在八万开走,虽然是大套手续,但面子给足了。”
老林把那串钥匙攥进手心,硬邦邦地回了一句:“我不图面子。”
出了二手车行的铁皮大门,外面的风有点大。那辆黑色的奔驰S级停在路边,车漆有些暗淡,左前灯罩上还有道不明显的划痕。
那是台抵押车,也就是俗称的“黑车”。原车主断了贷,车被抵押公司扣了,几经转手到了这儿。
“上车。”老林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
我站在车外没动:“我不坐。你买这玩意儿,回去怎么跟大伯他们交代?妈走的时候留的那点底子,你就这么造?”
提到我妈,老林握着方向盘的手僵了一下。他慢慢转过头,眼神混浊,眼袋在那张松弛的脸上挂着,显得格外疲惫。
“上车。”他又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多了几分不容置疑。
我拉开副驾门,坐了进去。车里有股陈旧的烟草味,混合着劣质车载香水的味道。
老林发动了车子。发动机的声音还算厚实,但他起步很猛,车身猛地往前一窜,差点撞上前车的保险杠。
“你会不会开?”我下意识抓紧了扶手。
“二十年没摸车了,手生。”老林淡淡地说。
车子汇入晚高峰的车流。堵车。红色的尾灯连成一片海。
我侧头看窗外,不想看他。车窗玻璃上映出老林的侧脸,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我想起三年前,也是这样的黄昏。妈还在。
那时候老林还没这么瘦,也没这么倔。那天我刚提了新房的钥匙,接他们二老去看房。
妈坐在后座,摸着真皮座椅,笑得合不拢嘴:“这车真稳,比你爸当年的那辆破摩托强多了。”
老林在前头呵呵地笑:“那是,儿子出息了。以后咱们老两口就跟着享福。”
那时候的老林,腰板是直的,说话声音是洪亮的。他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技术员,也就是个修机器的,但他总觉得自己手艺好,能撑起这个家。
妈去世那天,老林没哭。他只是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整夜。从那天起,那个会修收音机、会给妈做红烧肉的老林就不见了。
现在的他,只是个性格古怪、花钱没数、听不进人话的倔老头。
车子停在红灯前。老林突然伸手打开了储物格,摸出一盒压扁的硬盒红塔山。
“车里别抽烟,我闻着恶心。”我皱眉。
老林动作顿了顿,把烟放了回去。
“这车有定位。”我提醒他,“那些放贷的公司都有备用钥匙和GPS。你今天开走,明天他们就能顺着信号找过来,直接把车开走。到时候你钱车两空。”
“我知道。”老林目视前方,绿灯亮了,他踩下油门。
“知道你还买?”
“我有数。”
“你有什么数?你连智能手机都玩不明白!”我声音提高了几度。
老林没理我,车速提了起来。他把收音机打开,调到一个全是杂音的频道,然后又关掉。
回到老小区的楼下,天已经黑透了。那辆大奔挤在一堆电瓶车和老代步车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邻居王婶正好下楼倒垃圾,看见这车,眼睛瞪得滚圆:“哟,林师傅,这是……发财了?”
老林没搭腔,锁了车,径直往楼道里走。
我跟在后面,觉得脸皮发烫。王婶那眼神,分明是在看笑话。谁不知道老林家这两年日子过得紧巴,忽然弄这么个大家伙回来,不是脑子坏了是什么。
进了屋,家里冷锅冷灶。
桌上还扣着中午剩下的半盘咸菜和两个馒头。
老林进屋就开始翻箱倒柜。他把床底下的旧皮箱拖出来,灰尘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你找什么?”
“找地图。”老林头也不抬。
“现在谁还用地图?手机导航不行吗?”
老林没理会,从箱底翻出一张发黄的中国交通图。那是十几年前的版本了,上面的很多高速公路估计都没修好。
他把地图铺在桌上,用手指顺着一条线,慢慢地往西划。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刚才修车弄的一点黑油泥。
那条线穿过省界,穿过平原,一直延伸到那片褐色的高原区域。
“我要去这儿。”老林的手指点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地方连个地名都没有,周围是大片的空白。
“这是无人区。”我说,“你去那干嘛?送死?”
老林抬起头,眼神里有一股我不熟悉的冷光:“去找东西。”
“找什么?”
“找你妈丢在那的东西。”
我愣住了。妈这辈子最远就去过省城,什么时候去过几千公里外的高原?
“爸,你是不是糊涂了?妈没去过那边。”
老林把地图折起来,塞进怀里:“她去过。梦里去的。”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比糊涂更可怕,这是魔怔了。
“我不准你去。”我站起来,挡在门口,“明天我就把车退了,哪怕亏两万块钱也得退。”
老林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车在我名下。腿长在我身上。”

02.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楼下的嘈杂声吵醒的。
拉开窗帘,那辆黑色奔驰还在,但后备箱敞开着。老林正一趟趟往车上搬东西。
两桶大号的矿泉水,一箱压缩饼干,几件厚得像棉被一样的军大衣,还有那套他那年下岗时发的工具箱。
我套上衣服冲下楼。
“你真要走?”我拦在他面前。
老林把一捆尼龙绳扔进后备箱,拍了拍手上的灰:“今儿天气好,宜出行。”
“这车手续不全,上不了高速,出了省就被扣!”我拽住车门。
“我不走高速。走国道,走省道,走土路。”老林绕过我,坐进驾驶室。
我想拔车钥匙,但他动作更快,直接打着了火。
车窗降下来,老林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我心头一跳。
那眼神不像是个要去送死的老头,倒像是个要去赴约的战士。坚定,还有点解脱。
“家里水电费我都预存了。”老林说,“你那个新房要是还贷压力大,就把这老房子租出去。房产证在立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
“爸!”我喊了一声,“你到底要干什么?妈都走三年了!”
“是啊,三年了。”老林低声念叨了一句,“三年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他挂上档,松开刹车。车轮碾过地上的碎石子,发出咔咔的响声。
我追了两步,车子加速了,尾气喷了我一裤腿。
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小区拐角,我拿出手机,给大伯打了个电话。
“大伯,我爸走了。买了个抵押车,说要去高原。”
电话那头大伯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幸灾乐祸:“我就说老二脑子这两年不对劲。随他去吧,那么大岁数了,还能真开到那儿?估计出了城就没油钱回来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心里空落落的。
我又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肉。老林在厂里加班,半夜回来,怀里总揣着两个热乎的肉包子。
他把包子塞给我,自己啃冷馒头。
“儿子,吃肉长力气。以后长大了,带你妈去大城市转转。”
那时候的灯光昏黄,老林的笑脸很暖。
那个承诺,他记了一辈子。但我妈没等到。
妈走的那年,是肺癌。发现就是晚期。
医生摇头,说没治的必要了,带回家吃点好的吧。
老林不干。他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跪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求人家给用最好的药。
那一周,老林老了十岁。
最后妈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很痛苦,瘦得皮包骨头。老林握着她的手,一滴眼泪都没掉,就那么干坐着,直到护士来盖白布。
从那以后,老林就变了。他开始在这个家里变得透明,变得沉默。我们父子俩的交流,剩下的只有“吃饭”、“睡觉”、“交水电费”。
我以为他已经接受了现实,没想到他心里憋着这么大一个雷。
下午三点,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隔壁省的。
“喂,是林建国的家属吗?”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粗嗓门,背景音很嘈杂,像是在车上。
“我是他儿子。你们是谁?”
“哦,儿子啊。告诉你爹一声,那车是我们公司的资产。定位显示他出省了。让他赶紧停下,不然我们追上去,性质就变了。”
我心里一紧:“你们是收车的?”
“你可以这么叫。我们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清收队。这车也是他八万块能买断的?那是人家欠了一百多万抵给我们的!识相的让他把车停在最近的服务区,钥匙留车上,人滚蛋。”
“你们别乱来。”我握紧了手机,“我会劝他回来的。”
“劝?嘿嘿。”对面冷笑了一声,“我们两辆霸道已经在路上了。离他就五十公里。你最好祈祷他听劝。”
电话挂断了。
我赶紧给老林打电话。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一遍,两遍,三遍。全是关机。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老林这不是去旅游,这是在逃亡。
他为什么要关机?他是知道有人会追来,还是单纯不想让人找到?
我翻出手机里的定位软件。那是上个月为了防他走丢,我偷偷在他手机里装的。
屏幕上,一个小红点正在地图上缓缓移动。
位置显示,他已经进了山区。那是通往西部的必经之路,路况极差,只有两条车道,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沟。
红点的后面,大概几十公里的地方,我想象着有两辆满载壮汉的越野车,正像猎狗一样死死咬着不放。

03.
我请了假,开着我那辆开了五年的大众,往那个方向追。
我知道追不上,但我不能在家干等着。
路上,雨越下越大。雨刮器拼命地刮,还是看不清前路。
我又接到了那个粗嗓门的电话。
“你爹是属兔子的?跑这么快?”那人语气里带了点火气,“这老头不要命了?刚才那段盘山路,限速四十,他开八十!差点冲下去!”
“你们别追太紧!逼急了出事你们负责吗?”我对着蓝牙耳机大吼。
“负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车是我们的,他不停车就是抢劫!”
嘟嘟嘟。电话又挂了。
我看着导航上的红点。老林的位置已经过了省界,进入了邻省的山区腹地。那里人烟稀少,全是连绵的大山。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
我想起妈刚确诊那天,老林蹲在阳台上抽烟。我走过去,看见他手里的烟烧到了指头,他都没反应。
“爸,要是钱不够,我把房子卖了。”当时我这么说。
老林摇摇头,把烟头掐灭在栏杆上:“房子是你妈给你留的娶媳妇本。不能动。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去借遍了所有的亲戚。
大伯、三叔、甚至几年不走动的远房表亲。他低着头,弯着腰,陪着笑脸,一张一张地借钱。
那时候我也恨他。恨他的无能,恨这种把尊严踩在脚底下的感觉。
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他,至少还是个为了家在拼命的男人。
现在呢?他开着一辆随时会被抢走的车,往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跑,是为了什么?
天快黑的时候,我到了邻省的一个服务区。
我再次拨打老林的电话。通了!
“喂!爸!你接电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那边沉默了几秒,传来了风声,呼呼的,很大。
“爸!你在哪?那些人追上来了!你快停车,把车给他们,人回来!我去接你!”
“回不去了。”老林的声音很远,像是隔着很长的隧道,“到了这儿,就回不去了。”
“什么叫回不去了?你别吓我!”
“他们追不上我。”老林突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很干涩,“这路我熟。当年送货,这条路我跑了五年。”
我愣了一下。我想起来了,年轻的时候,老林是开过长途货车的。那时候妈还没生病,他跑一趟车回来,总能带回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的路不一样了!”
“路变了,山没变。”老林说,“儿子,好好过日子。别像我,窝囊了一辈子,临了才想起来该干点啥。”
“你到底要干啥?你去高原干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紧接着是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他们来了。”老林说了一句,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黑下去,手心里全是汗。
我站在服务区的雨棚下,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远处的高速公路上,只有零星的车灯划过。
我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像当年看着妈躺在病床上,看着监护仪上的线条变平,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时候,那个粗嗓门又打来了。
“操!这老东西!”那人骂骂咧咧的,“他把车开进小路了!那路前面塌方了,他也敢闯?”
“你们看到他了?”
“看见个屁!尾灯都看不见!这老头开车跟不要命似的,这哪是开大奔,这是开坦克呢!前面是土路,全是泥坑,我们的车底盘高都费劲,他那轿车居然没趴窝!”
“求你们别追了。”我声音软了下来,“让他停下,车给你们,我再补你们点钱行不行?”
“晚了!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这老头耍我们在山里转了三个小时!今天不把他截住,老子这行以后没法混!”
挂了电话,我只能继续盯着那个定位软件。
红点在地图上一片没有任何道路标识的区域缓慢移动。那里应该是废弃的林道或者是牧民走的小路。
老林,你到底在想什么?
04.
这一夜,我是在车里度过的。
我不敢睡,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定位。
红点还在动,但是速度很慢。凌晨三点的时候,红点停在了一个山口附近,不动了。
我心提到了嗓子眼。是没油了?还是被追上了?或者是……出事了?
我试着打那个粗嗓门的电话,没人接。打老林的电话,关机。
天亮的时候,我到了那个山口附近的一个小镇。
这里已经是高原的边缘了。空气稀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镇上的派出所很简陋,只有一个老民警在值班。
我冲进去报案:“警察同志,我爸失踪了,有人在追他!”
老民警看了我一眼,慢悠悠地倒了杯水:“失踪多久了?”
“昨天下午到现在联系不上。最后定位就在前面那个山口进去三十公里。”
“三十公里?”老民警皱了皱眉,“那边是老林区,早就封山了。里面没信号,路也断了。除了偷猎的,没人往那钻。”
“有人追他!是放高利贷收车的!”
老民警神色严肃起来:“非法讨债?几个人?什么车?”
“两辆越野车,大概五六个人。”
正说着,门口停下了一辆满是泥浆的霸道。
车门开了,下来三个男人。领头的正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粗嗓门,但他现在的样子很狼狈。
衣服上全是泥,脸色发白,像是刚生过一场大病。另外两个人扶着车门在呕吐。
我一眼认出了他,指着他对警察喊:“就是他们!他们追的我爸!”
老民警手按在腰间的执法记录仪上,走过去:“干什么的?”
粗嗓门看见警察,没有跑,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哆哆嗦嗦地掏出烟,点了三次才点着。
“警察同志,我们……我们自首。”粗嗓门声音发颤。
我冲过去抓住他的领子:“我爸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粗嗓门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恐惧。那种恐惧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真切切被吓破了胆。
“我们没把他怎么样……”粗嗓门咽了口唾沫,“我们跟到半路,就……就回来了。”
“放屁!你们不是说要截住他吗?车呢?人呢?”
“车……车还在里面。”粗嗓门指了指大山深处,“还在那个山谷里。”
“那人呢?”
粗嗓门摇摇头:“不知道。车在那,人没了。”
“什么叫人没了?”我脑子嗡的一声。
“就是……不见了。”旁边一个小弟插嘴道,脸青得像死人,“车门开着,发动机还是热的,就是没有人。周围也没有脚印。”
“不可能!”我吼道,“刚下过雪,怎么可能没脚印!”
“真的没有……”那个小弟带着哭腔,“而且……而且我们在车后座上,看到了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老民警追问。
三个大汉互相对视了一眼,谁都不敢说话。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05.
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所长亲自坐镇,我和那个老民警坐在旁边。
粗嗓门坐在铁椅子上,手铐碰着桌面发出哗啦的响声。他已经喝了两大杯热水,还是止不住地打摆子。
“说清楚。”所长敲了敲桌子,“你们非法追车,导致当事人失踪,这是大案。如果人出了事,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所长,我真没动他。”粗嗓门急得快哭了,“我们是干清收的,图的是车,不是命。杀人偿命的事我们不干。”
“那你们为什么跑回来?”所长盯着他的眼睛,“既然车都找到了,为什么不开回来?那车值不少钱吧?”
粗嗓门缩了缩脖子:“不敢开。”
“不敢?”
“对,不敢。”粗嗓门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讲一个恐怖故事,“我们追了他一路。那老头真他妈是个疯子。那种断头路,旁边就是悬崖,他敢闭着眼往里冲。我们底盘高,好几次都差点翻下去。”
“讲重点。”
“后来,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我们看见他的尾灯停在那个山坳里了。那地方邪门得很,风吹得呜呜响,像有人在哭。”
粗嗓门顿了顿,眼神开始发直。
“我们想着,这回他跑不掉了。我就带着兄弟们围上去。车停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大灯还亮着,直直地照着前面的一棵枯树。”
“我们拿着棍子,喊他下车。没人应。我们就去拉车门。门没锁,一拉就开了。”
“驾驶座上是空的。”
“我当时想,这老头肯定躲附近林子里了。我们就拿着手电筒找。可是……地上只有那辆车的车辙印,没有人的脚印。真的,警察同志,那雪地上平平整整的,连个鸟爪印都没有,他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这不可能。”所长皱眉,“除非他会飞。”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但我看了一圈,真没有!然后……然后顺子,就是跟我那个小弟,他去翻后座,想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粗嗓门吞了口唾沫,声音压得极低:“顺子叫了一声,吓得坐地上了。我过去一看,后座上放着个打开的箱子。”
“箱子里是什么?”我忍不住插嘴。
粗嗓门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既有同情,又有恐惧。
“箱子里……是一堆石头。彩色的石头。”
“石头?”我愣住了。
“对,但我仔细一看,那不是普通的石头。”粗嗓门的声音颤抖起来,“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字。用红油漆刻的。我拿起来一块,上面刻着一个日子。”
“什么日子?”
“2021年3月15日。”粗嗓门看着我,“兄弟,如果我没记错,那是……”
我脑子“轰”的一声。2021年3月15日,是我妈去世的日子。
“还有呢?”老民警问。
“还有很多块。上面刻的都是日子,还有地名。全是……医院的名字。”粗嗓门继续说,“但最吓人的不是这个。是在那个箱子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你爸,还有一个女人,就是你妈。背景就是那个山坳,就是那棵枯树。但是那照片……那照片是黑白的,而且看着很旧很旧,起码有三十年了。”
“这有什么吓人的?”所长问。
“吓人的是……”粗嗓门身体前倾,瞳孔放大,“那照片上,除了他们俩,背景里的那棵树上,还吊着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粗嗓门张大了嘴,刚要说出那个词,突然审讯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一个年轻警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张传真纸。
“所长!查到了!那个老林的身份查到了!还有那辆车的前前任车主信息也出来了!”
所长接过纸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粗嗓门,又看了看我。
“不用问了。”所长把纸拍在桌上,声音冰冷,“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收那辆车了。”
那张传真纸上的字被红笔圈得死死的。
“车辆识别代码显示,这辆车是四年前一桩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的涉案车辆。当时的肇事者,就是这家抵押车行的老板,赵天霸。”
所长把纸往桌上一扣:“这车根本不是抵押物,它是那个姓赵的想要销毁的证据。他以为风头过了,把车改了色套了牌放出来卖,没想到被你爸买走了。”
那个粗嗓门听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脸如死灰:“完了……怪不得老板听说车被开去无人区,急得亲自开车追过来……”
我猛地站起来:“你说什么?你们老板也来了?”
粗嗓门哆嗦着点头:“他在后面那辆陆巡上。那是他的命门,他肯定得去。”
我看了一眼窗外黑沉沉的大山。老林不是在逃跑,他是在钓鱼。
06.
我没等派出所的安排,转身冲出了门。
我知道老林在哪。
那个粗嗓门提到的“枯树”和“山坳”,我小时候在老林画的画里见过。那是他年轻时在西北地质队修车的地方。
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皮卡,车主是个穿着羊皮袄的本地汉子,正蹲在地上抽旱烟。
“大叔,车租给我,去趟狼沟。”我把钱包里所有的现金都掏出来,塞给他。
汉子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我:“狼沟?那地方早就没路了,只有野驴才往那钻。”
“我有急事,救命的事。”
汉子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吐出一口白烟:“上车。那地方我熟,但车坏了你得赔。”
皮卡轰鸣着冲进夜色。
路上,我脑子里全是老林那张平静的脸。
他买车时没看合同,但他看了车底盘。他在家擦车时,不仅仅是在擦灰,他是在检查。
老林干了一辈子机修,耳朵比雷达还灵。发动机有没有异响,大梁有没有动过,他一摸就知道。
他肯定在车上发现了什么。
“小伙子,坐稳了!”汉子喊了一声,方向盘猛打。
车子拐进了一条满是碎石的河滩路。颠簸得我五脏六腑都在颤。
“前面就是狼沟口。”汉子指着远处两座像獠牙一样的山峰,“以前这儿有金矿,后来矿塌了,就没人来了。听说里面闹鬼。”
“不是鬼。”我抓着扶手,咬着牙,“是人心里的鬼。”
我想起粗嗓门说的那个“吊着的东西”。
那是老林的手段。他在厂里当保卫科长的时候,就专门抓那些偷铜缆的贼。他知道怎么让人害怕。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辆霸道。
车翻在路边的沟里,四个轮子朝天,冒着黑烟。
汉子停下车,我跳下去看了一眼。车里没人,地上有血迹,杂乱的脚印往山谷深处延伸。
“前面车进不去了。”汉子从后座抽出一把扳手递给我,“拿着防身。”
我接过扳手,沉甸甸的,冰冷刺骨。
“谢了。”
我顺着脚印往里跑。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但我感觉不到疼。我只怕晚一步。
07.
山谷里静得吓人。
转过一道弯,我看到了那棵枯树。
那是一棵巨大的胡杨,早就死了,枝干像鬼爪一样伸向天空。
而在树下,停着那辆黑色的奔驰。
车门大开,车身满是泥泞,像一头力竭的野兽。
我慢慢靠近。
粗嗓门没撒谎。后座上确实放着那个箱子,里面全是刻了字的石头。
我拿起一块。红油漆写着:2020.12.01,省人民医院,化疗。
又拿起一块:2021.01.15,ICU,欠费两万。
这些石头,是妈受罪的日子,也是老林心里的钉子。
而在箱子底部,压着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老林搂着年轻的妈,笑得灿烂。背景就是这棵树。
那时候,树还活着,叶子是金黄的。
“别动那个箱子。”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猛地回头。
老林就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块岩石后,身上披着那件旧军大衣,手里拿着把大号的管钳。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但眼神亮得吓人。
“爸!”我鼻子一酸,想冲过去。
老林摆摆手,示意我别动:“别过来。前面有陷阱。”
“陷阱?”
“那帮人已经进去了。”老林指了指枯树后面的一个废弃矿洞,“那个姓赵的老板,贪心,想要回他藏在车里的东西。”
“车里有什么?”
“A柱的夹层里,藏着个账本,还有当初撞人后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卡。”老林淡淡地说,“他以为这车报废了就没事了,后来想卖钱又舍不得拆,结果落到我手里。”
“你早就知道?”
“买车的时候不知道。回来修车灯的时候摸出来的。”老林咳嗽了两声,“我看了那个内存卡。那年你妈骑车去买菜,被撞倒在路边,那辆车停都没停就跑了。”
我浑身一震。
妈当年的腿伤,就是因为那次车祸。虽然后来是因为癌症走的,但那次车祸后她身体一直不好,落下病根。
原来肇事者就是这个赵天霸。
“我本来想直接报警。”老林看着那个矿洞,“但那样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自己走进来,让他知道什么叫怕。”
08.
矿洞里传来了惨叫声。
“啊——!救命!”
是那个赵天霸的声音。
“怎么回事?”我问。
“那个洞以前是存放炸药的,地基早就空了。”老林面无表情,“我昨天在门口挂了点东西,那个收车的胆小,吓跑了。这个姓赵的胆大,也是急眼了,直接冲进去找东西。”
“你挂了什么?”
“你妈织的一条红围巾。那是她当年给你准备结婚用的。”老林从怀里掏出一条红色的围巾,拍了拍上面的灰,“那些心里有鬼的人,看什么都像吊死鬼。”
这时候,矿洞口跌跌撞撞跑出来两个人。
正是赵天霸和他的一个保镖。赵天霸腿好像断了,被保镖架着,满脸是血。
他一抬头看见老林,眼睛瞪得滚圆:“老东西!你阴我!”
保镖掏出一把弹簧刀,冲着老林就比划:“把东西交出来!不然弄死你!”
老林坐着没动,手里的管钳在石头上轻轻敲着节奏。
“东西在车里。有本事自己去拿。”
赵天霸推开保镖,红着眼往车边挪:“快!去拿!拿到我们就走!”
保镖冲向奔驰车。
我握紧了手里的扳手,刚要冲上去,老林喊了一声:“趴下!”
我下意识地往地上一滚。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那个保镖刚拉开车门,车底盘下突然弹起一根粗大的尼龙绳,直接套住了他的脚脖子。紧接着,绳子另一头绑着的一块百斤重的大石头从树上坠落。
利用滑轮原理,保镖整个人被倒吊了起来,悬在半空中哇哇乱叫。
那是老林以前在厂里做起重设计时的绝活。
赵天霸吓傻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往后蹭:“你……你到底是谁?”
老林慢慢站起来,提着管钳,一步一步走过去。
风吹起他的军大衣,猎猎作响。
“我是个修车的。”老林走到赵天霸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也是个当丈夫的。”
09.
赵天霸崩溃了。
在这荒无人烟的无人区,手机没信号,手下被吊着,面前站着个不要命的老头。
“大爷!叔!我错了!”赵天霸跪在地上磕头,“当年那事是我不对,我赔钱!我有钱!我给你一百万!不,两百万!”
老林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嫌少?五百万!只要你把那个内存卡给我,我马上转账!”
老林弯下腰,从兜里掏出那个小小的黑色内存卡,捏在指尖。
“这东西,能换五百万?”
“能!绝对能!”赵天霸眼里放出贪婪的光。
老林笑了。那笑容里全是轻蔑。
“这东西,换不回我老婆的一条腿,也换不回她后来遭的罪。”
说完,老林手一扬。
内存卡划出一道弧线,落进了旁边深不见底的山涧里。
“不!”赵天霸惨叫一声,想要扑过去抓,却扑了个空,脸直接磕在碎石上,血流满面。
我也愣住了:“爸!那是证据!”
老林转过头看着我:“真的证据,我早就寄给省里的督察组了。刚才扔的,是咱家行车记录仪里的卡。”
赵天霸听完,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一样,瘫软在地。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
远处,隐约传来了警笛声。
虽然这里是无人区,但老林出发前留下的后手,还有那个粗嗓门的自首,终于引来了正义。
官方的人来得很快。
几辆越野警车卷着尘土停在路口。身穿制服的人员迅速控制了现场。
赵天霸被戴上手铐拖走的时候,还在歇斯底里地喊:“疯子!一家子疯子!”
老林没理他。他走到那棵枯树下,把那条红围巾小心翼翼地系在树枝上。
风一吹,红围巾飘起来,像是一团燃烧的火。
“老婆子,看见了吗?”老林拍了拍树干,“当年的债,讨回来了。”
10.
下山的时候,是我开的车。
那辆奔驰作为证物被拖走了。老林坐在我那辆破大众的副驾上,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呼噜声打得震天响。
这是三年以来,我第一次见他睡得这么踏实。
我看着他的侧脸。
胡子拉碴,满脸沟壑,头发花白。这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技术员,也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家庭煮夫。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个家的男人。
回程的路很长。
我们在服务区停下吃东西。
我点了两碗牛肉面,加了双份肉。
老林狼吞虎咽地吃着,汤汁溅在胡子上也没擦。
“爸。”
“嗯?”老林抬起头,嘴里塞满了面条。
“那八万块钱……大伯他们肯定要念叨。”
老林把碗放下,抹了一把嘴:“念叨就念叨。车没了,钱也没了。但我这心里头,干净了。”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卡,推到他面前。
“这是我和媳妇存的一点钱。本来想换车的,现在不用了。这钱你拿着,把欠亲戚的账还了。”
老林愣了一下,推回来:“不要。我有手有脚,回去找个修理厂……”
“拿着!”我按住他的手,“我是你儿子。这钱不是给你的,是替妈给你的。”
老林的手抖了一下。他低下头,盯着那碗面汤。
过了好久,我看见有一滴水珠落在汤里,荡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好。”他声音哑哑的,“回家。”
11.
赵天霸的案子判得很快。
涉黑、非法放贷、交通肇事逃逸,数罪并罚。虽然具体的判决书我没细看,但我知道,这辈子他是别想出来了。
那家二手车行也被查封了。听说受害者排着队去登记。
那个粗嗓门因为有自首情节,加上只是从犯,判得轻点。
老林成了小区的名人。
王婶再也不用那种看笑话的眼神看他了。每次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林师傅”。
但我知道,老林不在乎这些。
他把家里的那些老旧家具都擦得锃亮。
那张地图被他重新收进了箱底。
那个装着石头的箱子,并没有带回来。老林把它埋在了那棵胡杨树下。他说,那是妈最喜欢的地方,让她在那看着,这世道还有没有公道。
周末,我带着媳妇回家吃饭。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红烧肉香味。
老林系着围裙,正在厨房里忙活。
“爸,做什么呢这么香?”媳妇笑着问。
“红烧肉!你们妈以前最爱吃的那种做法。”老林端着盘子出来,脸上的皱纹仿佛都舒展开了,“多放糖,少放盐,火候要足。”
我们围坐在桌边。
桌子中间,摆着妈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小碗红烧肉。
老林倒了一杯酒,先洒了一半在地上,然后自己滋溜一口干了。
“吃饭。”老林敲了敲碗边,“多吃点,吃肉长力气。”
我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还是那个味道,那个童年记忆里,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味道。
我看了一眼老林。
他正给媳妇夹菜,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哪个菜市场的肉新鲜。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白发上,泛着暖暖的光。
我突然明白,那个买抵押车闯无人区的老林,和眼前这个做红烧肉的老头,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人。
他没有疯,也没有变。
他只是在用尽全力,爱着这个家,爱着那个先走一步的人。
12.
半年后。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西部的信。
寄信人是那个借我皮卡的藏族大叔。
信封里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那棵枯死的胡杨树。
神奇的是,在那个系着红围巾的树枝旁边,竟然长出了一簇嫩绿的新芽。
在那片寸草不生的荒漠里,这簇新芽绿得耀眼,绿得顽强。
我把照片递给老林。
老林戴上老花镜,看了许久。
他没说话,只是走到阳台上,给那一盆快要枯死的吊兰浇了点水。
“春天到了。”老林看着窗外,轻声说。
楼下的公园里,一群孩子正在放风筝。那风筝飞得很高,很高,线虽然细,但一直牵在手里,从未断过。
就像我们这个家。


“17岁少年如何被毛泽东一手培养成‘红军铁屁股’?背后真相令


长期上门回收西门子阀门定位器


皇马变天:阿隆索不靠巨星靠体系,三招让银河战舰脱胎换骨


内蒙赤峰市公积金提取:这三点要求是关键!


甄嬛合影曝光:孙俪坐C位背后的咖位与情谊,你看懂了吗?


2025年最建议买的面膜品牌:探寻水润与活力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