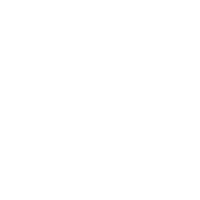《一段与江青相关的历史记忆》
发布日期:2025-11-24 15:20 点击次数:159

自左而右,依次为林利、一位苏联籍的保健护士、江青以及张国男。
张国男是李公朴的女儿,1948年在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分到该校外语系学俄语。
1951年新春伊始,军委卫生部所属的北京医院迎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他们肩负着为中央首长诊疗的重任。医院急需两名党员翻译,我和陈复君同学因此得以提前一个学期完成学业,卸下了灰色的制服,换上了绿色的军装,肩负起北京医院保健翻译的重任。
1952年夏日某日,我接到了一项指令:将陪同江青女士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并担任其翻译一职。
在启程之际,军委卫生部傅连暲部长亲自对我进行了叮嘱:在出差期间,严禁与家人联络,所有信件将由大使馆的信使代为转达。同时,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次出差的具体任务。此次任务,我不仅要胜任翻译一职,还需负责对江青同志的服务工作。归来后,我需直接向您汇报。
9月6日,我身着鲜艳的红花连衣裙,褪去了绿军装,被送往南苑机场。那里,一架苏联的专机正整装待发。就在这时,毛主席与江青从一辆轿车中步出。
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是真心关爱。
已近四十岁的江青着装得体,步履间显得腰杆挺直,举止间流露出几分风度。她素颜出行,却让人感觉格外舒心,待人接物亲切平和,让我原本的紧张情绪得以消解。
苏联的专机设施考究,配备了卧室与客厅,自飞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起,我便与江青一同领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尊贵待遇。
飞机于途中在伊尔库斯克短暂停留,进行加油,随后再续征程。当夜幕低垂,抵达莫斯科。迎接我们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她乘坐的黑色吉斯车在沿途红灯处可享绿灯通行之优待,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的特权。车辆径直驶向克林姆林宫医院——我国同志称之为“皇宫医院”,仅对国内外的高级干部开放。
病房设有内外两室,内室宽敞,专供患者居住;而外室则相对狭小,是为家属或陪护人员所设。
在病房中,一位保健医生早已等候,立刻为江青完成了长途跋涉后的必要体检。
数日细致的检查后,专家得出结论:江青女士患有泥沙状的胆囊结石,治疗方案为胆囊冲洗。治疗时,患者需采取右侧卧位,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经口腔插入胃部,直至幽门,并顺利抵达胆囊。此过程颇具挑战,精确调整姿势至关重要,以确保引流管能够顺利穿过幽门,直达胆囊内部。
在引流操作中,江青时常需借助管子发声,起初我对其言语难以辨识,以致翻译受阻。医生焦急万分,患者亦倍感不安,这无疑干扰了冲洗的常规流程。幸好,我迅速适应,不久便能够准确理解其话语。
经过数个疗程,泥沙的痕迹已几乎难以寻觅。遵循医生的指导,我们抵达了位于高加索地区的索契,一家专注于泥疗的专业疗养院。在那里,我们每日将黑泥敷于江青的腹部,以此实施泥疗。
二月,林利随同父亲——中央的老一辈领导人林伯渠——重返莫斯科的“皇宫医院”,不久后,她也肩负使命抵达了这家医院。林利,林伯渠之女,于1938年6月高中毕业后前往莫斯科深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延安。1949年以后,她多次随同高级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当年,她作为翻译参与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到了1952年的秋季,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林利再次担任翻译。大会结束后,她陪同刘少奇夫妇前往高加索的索契接受治疗,而江青当时也正于彼处进行泥疗。
江青邂逅了林利,遂对她说:“与那些人共事又有何趣?不如跟我同行。”回到莫斯科后,江青责令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林利谈话,力邀她留下陪伴自己。在江青的坚持下,林利不得不搁置了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任务,答应留下来。
本次入住的病房除了设有病人卧室外,还配备了宽敞的休息区域,供陪同人员居住。此外,还有一间兼具客厅与电话间功能的空间,同时也用作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场所。我国苏方安排了两名警卫员轮流值班。
林利心想,江青终究与毛主席不能同日而语,她此行是为了疗疾,于是他提议江青主动向苏方提出免去专门的警卫员安排。江青闻言虽显不悦,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然而,当时苏方依旧坚持为她派遣了警卫员。
3月5日拂晓,护士开始为江青进行胆汁抽取,以备化验。若一切顺利,她便可以返回祖国。就在这时,苏共中央的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匆忙闯入我的居所,急切地要求我立刻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通知江青。我婉言请求,希望能在完成胆汁引流后再透露这一噩耗,以免她的情绪过于激动,影响手术的进行。林利和医生也达成共识,决定暂时对江青隐瞒这一消息。
卡尔东诺娃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地诉说着,今日全球理应共知,苏联人民及党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她此行乃党中央所派,专程来向江青传达这不幸的消息。她步入江青的居所,请求林利协助翻译,并坚称林利与医生决定暂时对她隐瞒真相,实乃一项严重的政治错误。
江青情绪失控,痛哭流涕,一边哭泣一边用力拍打林利的桌子,痛斥其隐瞒了真相。待她情绪稍微平复后,医生仍为她进行了胆汁引流手术。
事后,江青向林利表达了她对林利及医生美意的充分理解。
数日之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下达通知,指示江青携我及林利一同前往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尽管这仅是短暂的几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却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后,江青感到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时常感到肝区疼痛,便计划待天气转暖之后前往南俄修养。林利把握时机,将国内单位同事寄给她,希望她归来的多封来信展示给了江青。江青对此极为愤怒,对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领导师哲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指责是他指使他人撰写了这些信件。
林利随后动员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共同劝说她,允许林利离去。江青最终点头应允。然而,到了起飞当日,江青失声痛哭,执意不放林利离开。
此刻,医生和护士长想方设法平息了江青的歇斯底里,最终允许林利离去。在告别之际,林利向我透露,江青声称你的爱人曾是沈钧儒的秘书,属党内民主派人士,她还提及你的社会关系颇为繁杂。
彼时,我与林利均深感困惑,难以置信江青竟会如此看待我。
直至“四人帮”的相关资料公之于众,方才知晓江青对提及她前夫唐纳之事极为忌讳。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这三对新人曾于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当时由著名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而著名导演郑君里则身兼司仪与摄影师两职。
江青不愿人知这段过往。
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一经报纸公开发表,便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江青对毛主席坦诚道:“您思念杨开慧,我则怀念着唐纳。”
盛怒之下,她匆匆给郑君里寄去一封信,恳求他提供唐纳在法国的通讯联络方式。
在与江青的交谈中,我随意提及了唐纳近况。不料江青面露不悦,未予回应。此番对话便成了我被她冠以“社会关系复杂”标签的契机。
在养病的日子里,江青常常挑选电影观赏,其中译制片《红与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幸而我曾阅读过这部经典名著,得以边观看影片边进行翻译,勉强度过了那段时光。
观赏完苏联制作的影片《第四十一》之后,她不禁向我感慨道:“这真是一部禁止公映的电影,实在令人惋惜。男女主演的表演可谓是出神入化!”
江青曾莅临大剧院观赏一场芭蕾舞表演,正值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演绎《红罂粟花》,她却直言不讳地表示:“此舞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们不宜观看。”至于普列谢茨卡娅,她的艺术成就仅次于乌兰诺娃,我们便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中,一同领略了由她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的风采。
再度观摩了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达拉索娃倾情演绎的《三姊妹》。演出结束后,她戏谑地对我说:“歌声倒是不错,只是形象略显不足,太过丰腴,我几乎难以忍受。虽想中途退场,却又担心包厢空荡无人的影响不佳。”
“瞧他们那大国沙文主义的思维多么显眼,我们即便在他们面前,也不可轻易示弱,关键时刻,我们同样需要勇敢地予以回击。”她始终如此付诸实践。
我们在此享受的待遇,与政治局委员的标准无异。在别墅中,每位成员每日可获100卢布的住宿费用,而住院费用则另行计算。江青曾向我言道:“在这里的花销,全由他们负责管理。鉴于我国外汇储备有限,我们都不应申请出差补贴。”
某日,她在信中获悉,协助她打理家务的姐姐之子成功考入了北京的一所知名学府。于是,她委托我协助她拨打汪东兴的电话。电话那头,她急切地询问外甥是如何被这所大学录取的,直至对方明确地告诉她,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的,她这才在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
她言辞恳切地对我说:“无论我们从事何种事务,都必须深思熟虑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明显察觉到,无论身处何地,她总是深思熟虑其言行的影响。她的着装得体大方,发型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尽管她有着罗圈腿的缺陷,但每一步行走都显得身姿挺拔,站立与就坐都保持着端正的姿态,连进食也都显得仪态万千,彰显着她独特的风范。
江青料想不会在苏联度过炎炎夏日,因此我们手头仅备有冬装。她吩咐我拨通汪东兴的电话,请他帮忙联系王光美,为我们挑选几段适合制作连衣裙的绸缎面料。她已提出了一些色彩选择。鉴于王光美的审美品味颇高。面料选购妥当后,便委托访苏代表团代为带回。苏共中央设有专为高级干部定制的裁缝服务,夏装制作得颇为迅速。
随着夏日的脚步渐近,江青携我及两位安保人员一同乘坐火车抵达了黑海边著名的疗养胜地——雅尔塔。我们安顿在一座风景秀丽的别墅中,那里距离碧波荡漾的大海仅有咫尺之遥。
贺子珍对孩童并无特别的喜爱,她的女儿姣姣,乃是我自农夫手中所收养,亦随我姓,名李敏。自幼便被送往苏联,归来后,她对中文的掌握已略显生疏。她不愿前往母亲处,更偏爱留在我家中。
在与她的对话中,她总会自豪地提及自己全方位地效仿主席,无论是书法还是签名。她曾多次当众挥毫泼墨,展示给我看,并询问我是否觉得她的模仿足够逼真。在我给出肯定的评价后,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得意。此外,她还致力于学习主席勤奋阅读的榜样。
随着盛夏的尾声悄然降临,两位安保人员屡次敦促我向江青提出启程返回莫斯科的请求,理由是天气转凉,不利于健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始终未予同意。
数日之后,我又被要求向江青提及返回莫斯科的请求,她最终虽不情愿,却也勉强予以了许可。
八月的莫斯科,气候如同北京深秋一般,江青由于两地温差显著,不禁有些感冒不适。她把我叫到身边,气急败坏地说道:“分明是你和保卫员二人,都急于想回家,竟然暗中勾结,编造出一大堆借口,催促我返回莫斯科。”
返身步入卧房,我不禁泪流满面,呜咽之声隐忍于喉头,生怕扰动了隔壁的服务人员,故而未曾放声大哭。
我天性较为豪迈,不拘小节。自从父亲离世,我只在那一刻放声大哭,此后便再未曾泪流满面。然而,这次江青注意到我那红肿的眼眸,责备我忽视形象,生怕旁人会误以为我遭受了她的欺凌。
9月初,我终于迎来了返回北京的时光。她特地对我言道:“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与你探讨我的近况,我对他并无好感,他总是事事插手,事事好奇。除了病情之外,其他的一切请勿提及。这真让我陷入了两难,我究竟该如何向他汇报呢?”
我们再度乘坐专机,该机为苏联制造的图—104喷气式客机。此次行程,她的保健女医生以及两位保卫人员全程陪同,确保她的安全。目的地直指北京。
出乎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的意料,飞机尚未完全停稳,毛主席便已向我们挥手致意。
跟随江青的脚步,我们一同走下飞机。毛主席依次与众人握手致意,待我介绍完三位陪同人员后,飞行员也加入了行列。毛主席一边与他们握手,一边关切地询问。
“我尚未体验过贵公司的喷气式飞机,能否让我上去体验一番?”
机长答道:“当然。”
主席健步流星地迈向飞机,登机稍作停留,随即神采飞扬地走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众人言道:
“我也坐过图104。”
数日之后,江青为表达对过去一年治疗与休养期间的悉心照顾的感激之情,特设宴款待了所有陪同人员。我向傅部长进行了工作汇报,荣幸地获得了对其工作的认可,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我的使命。
1955年新春伊始,我的长女王力平降临人世。得益于母乳的充足,她的成长态势良好。然而,在5月初,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使命——陪同江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这无疑意味着,我必须忍痛割舍,放弃为我心爱的女儿提供最优质的滋养。
随着出行日期的日益临近,我们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断奶。按照我院苏联专家的建议,我采用了用绷带紧束胸部的做法。当时我正处于发烧状态,在天津知名妇科专家俞霭峰教授的陪同下,我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通常我并不容易晕机,但这次在飞机上却剧烈呕吐,所幸得到了俞教授的悉心照料。
原本,江青的诊疗工作是由协和医院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负责,然而,她觉得林教授的诊疗手法过于粗暴,且言语间缺乏温柔,对她并无好感,因此她选择了俞教授作为她的主治医师。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1956年五月,江青完成了放射治疗疗程整整一年,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进行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她的精神状态亦颇佳。苏共中央特意安排了一次会面,以庆祝江青的康复。此次会见共有四位贵宾出席:斯大林继任者,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以及米高扬的夫人。
马林科夫的妻子在四人中年纪最轻。她自述担任电力学院的院长一职,并好奇地询问江青未来的志向及所学。得知江青学历有限后,她向江青提议:“不妨考虑加入我们学院深造。”江青听后,先是一愣,随后回应道:“若有机会,我定会前往贵学院学习。”这次对话似乎并不融洽,很快便草草收场。
驱车返回别墅途中,江青向我感叹道:“这些夫人们的素养实在令人失望,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夫人,她的言谈举止毫无分寸,竟敢建议我去她的学校就读,真是荒谬至极,她的傲慢无礼令人难以忍受。相较之下,赫鲁晓夫的夫人则显得更为朴素和蔼。这次会面严重伤害了江青的自尊,她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后便返回了北京。”
在那之后的四年里,我与江青大约有过四次见面,前三次均是她前往北京医院进行胆汁引流手术。她邀我来此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坚信我能够判断出何种卧姿能让引流管顺利穿过她的胆囊;二是她含着引流管说话时,我能够清晰地理解她的言语。其中一次,是我院内科的张惠芬主任亲自召唤我前往,她那时的表情充满了无奈,那副模样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对我说:“我们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胆汁引流手术,但她依然对我们的技术抱有顾虑,坚持要我来请你一同前往。”
那是在1959年的最后时刻,我在与江青的交谈中不经意间提及,我所跟随的最后一任神经内科的苏联专家亦已离我远去。那些先前的翻译们,原本都具备医学背景,如今均已转行从医。而我,仅学得俄语一门,内心深处渴望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专攻某一领域。正当我与江青的会面不久,春节的钟声敲响,我忽然接到通知:江青邀请我赴中南海她家中共进晚餐。我依照规定的时间,骑着自行车从家中出发,抵达了中南海。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主席也一同加入了我们的晚餐聚会。
毛主席在与我交流一番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工作中,我们能够不断汲取知识,而要想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的知识,就必须广泛阅读。并非唯有进入大学,方可获取学问。我自己便未曾踏入过大学校门,江青同志亦是如此。这顿在高级别场合举行的晚餐,乃是由江青同志精心安排。显而易见,她此举意在消除我对于求学的渴望。或许,这亦是她对我多次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的一丝感激之情。”
1960年,遵照院党委的部署,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接受了一年的专业培训。归校后,我担任了病房专职党支部的副书记和书记职务。然而,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身为中层领导干部,不幸成为了造反派的目标,被迫在病房中从事擦地等体力劳动。
1967年,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卫士魏琳向我展示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详细记载了汪东兴与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以及上海两位专家对江青进行的会诊意见。根据会诊结果,客观检查显示,江青所主诉的症状并未如其所言那般严重。
因涉览记载江青病情的私密笔记,我疑虑其涉嫌泄密,遂被囚禁于医院地下室长达十个月之久。终以“泄密即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抗”之罪名,我被定作现行反革命,并被留党察看两年。相较之下,魏琳的遭遇更为凄惨,她曾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六年的漫长囚禁岁月。
1969年,我踏入五七干校的行列。年终之际,我有幸荣获北京医院连队的表彰,被评为杰出的“五七”战士。然而,这份荣耀仅持续了短短两个月,我便再次遭受变故,被扣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随之而来的是半年的禁闭生活,我成为了专政的对象,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投身于劳动之中。
1973年重返医院后,我被委以重任,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同时兼任医院医务处党总支书记。经过十五载图书馆工作的辛勤耕耘与数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图书馆学会认可了我的努力与贡献,授予我副研究馆员的职称。1987年,我正式离休。


157%关税喊完就说要访华,特朗普这波操作看懵全球


从国际垫底到主办大赛,中国狙击手碾压20国精锐!实战数据曝光


上海最新政策公布,工资变化背后有何深意


让赛车从 “贵族运动” 走向 “全民狂欢” 记比亚迪全地形赛


南海爆发惊天对峙!中国052、054王牌舰艇抵近菲家门口,印


195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谈黄克诚,闲聊时提到林彪:难道四平